
医海泛舟 第二十四期
浏览数:1493次 2023-01-05医海泛舟是我科推出的一个定期更新的资讯型栏目,旨在围绕目前较新的医学热点及问题,收集翻译相关的资料,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各医学爱好者以及医学专业人员的思考以及讨论。
本来我们来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功能性单心室患者行非心脏手术的麻醉管理进展”
单心室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心脏病,约占先天性心脏病的3%。临床工作中,真正的独立心室比较少见。较为常见的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心室伴随一个发育不良的心室,在心脏功能上由发育良好的单一心室独立供应体循环和肺循环,称为功能性单心室。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单心室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延长,70%左心室发育不良的患者可以生存至成年期。
单心室患者可能会在各个年龄阶段行非心脏手术,其独特的循环系统为麻醉管理带来挑战。Brown等研究表明,单心室患者行非心脏手术时的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11.8%。本文就功能性单心室患者行非心脏手术的麻醉管理作一综述。
1.单心室患者心脏分期手术和循环系统
多数单心室患者经历3次分期手术可达到平衡循环的目的,每次手术后会形成不同的循环系统。
Ⅰ期手术:Ⅰ期手术可分为肺动脉缩窄术、改良BT分流术和Norwood手术。Ⅰ期手术多在新生儿期进行,总体目标是:单心室能够为体循环提供泵功能,维持适当的血流,保证血液氧合;避免肺循环容量和压力过负荷,导致肺水肿和肺动脉高压的发生,为Ⅱ期手术做准备。Ⅰ期手术后,单心室仍同时为肺循环和体循环供血,心室容量负荷较大,易造成心力衰竭、心肌肥厚和心内膜下缺血。患儿多在4~10月时行Ⅱ期手术治疗。
1)肺动脉缩窄术。部分单心室患儿主动脉、肺动脉和动脉瓣发育都正常。在正常循环系统中,体循环压力明显大于肺循环;单心室患儿肺动脉接受单一心室的压力和容量负荷,肺循环压力高、肺血流多,可导致肺水肿、肺动脉高压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并发症。为避免高压力下肺血管的损伤,多在新生儿期行肺动脉缩窄手术,即通过缩小肺动脉直径,控制血流量,达到降低肺动脉压的目的。
2)改良BT分流术。部分患儿右心室发育不良伴肺动脉严重狭窄,由肺动脉进入肺循环的血液过少,这类患儿多依赖肺动脉导管通过主动脉向肺动脉分流来维持足够的血液氧合。一般选择Goretex管连接右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达到体循环向肺循环分流的目的。
3)Norwood手术。当患儿左心室发育不良伴主动脉狭窄时,为改善体循环缺血的症状,多采用Norwood手术。术中将肺动脉从左右肺动脉分叉前剪断,侧面剖开与细小的主动脉侧面相吻合,必要时利用人工补片加宽主动脉弓,达到右心室为主动脉供血的目的。断下来的肺动脉远端借助改良BT分流术的管道由体循环分流至肺动脉或通过右心室直接分流至肺动脉(Sano分流术)。
Ⅱ期手术:Ⅱ期手术目前多进行双向格林手术,即将上腔静脉切断,缝闭近心端,远心端与右肺动脉行端侧吻合,双肺均接受经上腔静脉回流的血液。下腔静脉的血液回流至心脏,不进入肺循环,不进行氧合。下腔静脉回流至心脏的静脉血与肺静脉回流至心脏的动脉血形成混合静脉血,进入体循环。
双向格林手术成功的前提是肺血管发育良好,肺循环阻力低。新生儿的肺动脉压较高,无法直接行双向格林术,需待3个月后肺动脉压降至正常水平后再行Ⅱ期手术治疗,这也是需要Ⅰ期手术进行过渡的原因。双向格林手术后,肺循环血液的驱动力不再依赖右心室的收缩。双向格林手术减少了体循环回流至心脏的血流量,减轻了心室前负荷;同时肺循环压力降低,大大降低了肺血管病变的发生,为Ⅲ期手术做准备。以往有Ⅰ期手术后直接行Ⅲ期手术的报道,但由于其死亡率高,目前多行Ⅱ期手术进行过渡。
Ⅲ期手术:Ⅲ期手术通常行全腔肺吻合术,即将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的血液直接引流至肺动脉,使得心腔内只有含氧量高的动脉血。Fontan循环的患者体循环和肺循环完全分离,体循环氧合得到改善;同时心脏的容量负荷也明显降低。Fontan循环常作为单心室患者的最终循环方式。虽然Fontan循环并不是最理想的血流动力学系统,术后患者的运动能力不足,肝功能受损,并随着时间逐渐恶化,生存率随年龄明显下降。但目前来说,Fontan循环仍然是该类患者最合理的选择。
2.单心室患者行非心脏手术的麻醉管理
单心室患者多行3次分期手术,存在4种不同的循环系统:原始循环系统、Ⅰ期手术后的循环系统、Ⅱ期手术后的循环系统和Ⅲ期手术后的循环系统。在行非心脏手术麻醉前,必须充分了解单心室患者的心脏手术方式和不同手术方式后形成的循环系统特点和生理机制,采取不同的麻醉管理策略。
原始循环系统行非心脏手术:除了具有平衡循环的患儿,多数患儿在出生后数小时或数日内需接受心脏手术。然而有些患儿合并气道或胃肠道异常,如:坏死性肠炎、气管闭锁、气管食管瘘等,则需要先行急诊非心脏手术。术前评估的重点是心脏,超声心动检查是必须的检查,可以帮助了解患儿的心脏畸形类型。
充分了解患儿心脏房室、血管、瓣膜的畸形类型和程度,了解异常解剖下心脏工作的病理生理原理,这是术中进行合理的循环管理的基础和关键。另外单心室患儿往往合并其他器官的发育异常,因此,肝、肾、肺等器官功能的评估也很重要。
术中管理的目标是维持心脏收缩力,维持体循环和肺循环平衡,预防心律失常,改善血氧饱和度。新生儿的心肌发育尚未成熟,心肌收缩力差,心肌的长度-张力适应性下降,因此对后负荷的反应性较差;单心室同时接受肺循环和体循环的血液回流,容量负荷也比较大。应选择对心肌抑制较小的麻醉药物,推荐使用氯胺酮等静脉麻醉药物进行快速顺序诱导,静脉麻醉药物的优势在于对心肌的抑制作用比吸入麻醉剂小,并且更适用于饱胃状态的患者。
当怀疑心肌收缩力降低时,可经中心静脉导管输注正性肌力药物,如:米力农、多巴酚丁胺、肾上腺素等。中心静脉穿刺应尽量选择股静脉,因为颈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置管后,如果出现血栓会影响后期心脏手术方式的选择。对于肺动脉导管依赖性的循环,为尽量维持体循环和肺循环血量的比例稳定,可持续输注前列腺素E1保持肺动脉导管的开放状态。
对于肺动脉严重狭窄的患儿,可适当升高吸氧浓度,一方面,高浓度氧可以保证肺循环血液的氧合;另一方面,高浓度氧可降低肺循环阻力,增加肺循环血容量。但对于主动脉狭窄的患者,过高的吸氧浓度会降低肺循环阻力,减少体循环血流量,造成组织缺氧。通气时常使用相对较低的吸氧浓度,维持SpO2 70%~80%,PaCO2 45~50mmHg。
Walker等研究表明,对于该类患者,不能以维持正常的血氧饱和度(>90%)为目标,维持SpO270%左右是比较适当的选择,只有当SpO2持续低于70%,才建议升高吸氧浓度。对于非肺动脉导管依赖性的循环,则不需要输注前列腺素E1,其可能会导致呼吸暂停。该类患者不存在肺循环和体循环大动脉的严重狭窄,肺循环和体循环血流比例(pulmonary to systemic blood flow ratio,Qp/Qs)可通过对调节体循环和肺循环血管阻力来维持均衡,具体循环管理策略同下文Ⅰ期心脏手术后行非心脏手术的部分。
Ⅰ期手术后行非心脏手术:Ⅰ期心脏手术后应避免行择期非心脏手术,但Norwood术后往往胃肠道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有行急诊非心脏手术的可能。心脏术前评估的重点包括:心脏收缩功能、体循环和肺循环血量和比例、瓣膜功能、肺动脉和主动脉的狭窄和通畅程度和分流管血流等。
另外合并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常伴肺动脉压升高,导致肺血流减少,体循环血氧饱和度降低,非急诊手术应推迟。术中循环管理的目标是在正常心输出量的基础上维持“平衡循环”,确保组织灌注和充分氧供。健康人肺循环和体循环血流量是稳定且相等的,称之为“平衡循环”。改良Fick公式可计算:Qp/Qs=(SaO2-SmvO2)/(SpvO2-SpaO2)(SaO2,动脉血氧饱和度;SmvO2,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pvO2,肺静脉血氧饱和度;SpaO2,肺动脉血氧饱和度)。单心室患者由于主动脉和肺动脉血氧饱和度相等,因此Qp/Qs=(SaO2-SmvO2)/(SpvO2-SaO2)。
Ⅰ期心脏手术后,肺循环和体循环都由单一心室供血,两者血流比例并不恒定,互相影响和制约。即当体循环血量增多时,肺循环被氧合的血容量减少,导致心室内混合血氧饱和度降低,体循环氧供不足;相反,当肺循环血量增多时,虽然心室内混合血氧饱和度升高,但进入体循环的血量减少,也会造成体循环氧供不足。
通过数学模型得到,当Qp/Qs等于或略小于1时,可以获得最好的组织氧供。假设SmvO2和SpvO2在正常生理范围内,SaO2在75%~80%时,被认为可以反映“平衡循环”,即Qp/Qs=1,因此维持SaO275%~80%常被作为术中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当SaO2高于85%或低于70%时,提示肺循环血流量和体循环血流量不平衡,需要通过调节肺循环和体循环阻力,达到“平衡循环”。
维持SaO275%~80%并不是循环平衡的金标准。心输出量降低时,在SaO2不变的背景下,SmvO2的下降被从肺返回增加的氧合血液量抵消,Qp/Qs实际是升高的。应警惕患儿的低心输出量,维持心脏正常收缩力。单心室由于接受体循环和肺循环的双重血量,容量负荷较重,容量过多会导致舒张末期压力和容量负荷增大,造成心内膜下缺血;另外心率过快会导致舒张末期心肌灌注不足,也易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发生室颤。
当怀疑心肌收缩力下降时,应及时给予正性肌力药物。在不确定心脏功能是否正常的情况下,SmvO2监测是确定“平衡”循环的有效辅助手段。监测上腔静脉血氧饱和度替代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因为在单心室生理学中没有真正的混合静脉血),同时监测SaO2和SmvO2两项参数可以更好的指导循环管理。
当SaO2=75%~80%和SaO2-SmvO2=25%~30%时,提示平衡循环(Qp∶Qs=0.7~1.5∶1),此时患者循环状态良好,不需要干预;当SaO2>85%~90%和SaO2-SmvO2=35%~40%时,提示肺血过多(Qp∶Qs>2~3∶1),原因可能与低肺动脉压、BT或Sano分流管过粗或主动脉狭窄有关,此时需要通过增加肺动脉压和体循环氧供来进行干预,增加肺动脉压的措施包括允许性低通气、轻度酸中毒和降低吸氧浓度(FiO20.17~0.19),增加体循环氧供的措施包括使用正性肌力药和维持红细胞压积>40%。
当SaO2<65%~75%和SaO2-SmvO2=25%~30%时,提示肺血过少(Qp∶Qs<0.7∶1),原因可能与高肺动脉压、BT或Sano分流管过细有关,此时需要通过降低肺动脉压和增加体循环氧供来进行干预,降低肺动脉压的措施包括过度通气、碱中毒、镇静、治疗肺不张和使用一氧化氮,增加体循环氧供的主要措施是使用正性肌力药;当SaO2<70%~75%和SaO2-SmvO2=35%~40%时,提示低心输出量,原因可能与心肌缺血、心室收缩功能障碍、主动脉瓣反流、后负荷过大(主动脉弓狭窄)有关,此时应采取措施降低氧耗,包括镇静、使用正性肌力药物和降低后负荷。
当患者发生心跳骤停,标准的心肺复苏(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在单心室患者的复苏效果较差,采用插入式腹部按压心肺复苏(inter-posed abdominal compression CPR,IAC-CPR)更有效。IAC-CPR即在标准CPR的基础上,在胸部按压放松时行一次腹部按压,压力在150~200mmHg之间,按压频率为100~120次/分,压胸与压腹交替进行。
与标准CPR比较,在BT分流的患者中应用IAC-CPR,肺血流量增加30%、心输出量增加21%、舒张压升高16%、收缩压升高8%、冠状动脉灌注压升高17%、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加17%;在Sano分流的患者应用IAC-CPR,肺血流量增加150%、心输出量增加13%、舒张压升高18%、收缩压升高8%、冠状动脉灌注压升高15%、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加14%。
Ⅱ期手术后行非心脏手术:双向格林手术后肺循环由上腔静脉血液回流供血,体循环血量是肺循环和下腔静脉血液的总和。双向格林手术后的循环系统比Ⅰ期术后的循环更加稳定,至少下腔静脉的回心血量可保证相对稳定的体循环血量。双向格林手术后Qp/Qs随年龄变化,新生儿时上腔静脉回心血量占总回心血量的49%;2.5岁时达到最大值55%;之后逐渐降低,至6.6岁时降至35%,因此,通常患者SaO2在75%~85%。
上腔静脉静脉血流减少是影响双向格林术后患者预后的关键指标。术前应评估上腔静脉、肺动脉及吻合口的通畅程度,评估心脏收缩力、房室瓣功能和肺动脉压。若患者术前SaO2<75%、CVP>20mmHg、PAP>15mmHg和EF<50%通常与不良预后相关,应特别注意。双向格林手术后患儿术中管理的重点是要保证足够的血液进入肺循环氧合,来保证机体对氧的需求。增加上腔静脉回心血量的方法包括:维持足够的前负荷、维持较低的肺循环阻力、避免胸内压的急剧升高、维持心肌正常的收缩和舒张功能、避免心律失常。
胸内压过高会导致上腔静脉回流减少,因此保留自主呼吸可能比机械通气更加有利;如需要机械通气,应尽量保持较低的气道压,谨慎使用PEEP。术中应给予预防性止吐药物和长效镇痛药物,避免术后恶心呕吐和疼痛躁动引起胸内压的剧烈变化。王芳等认为,术中应避免通气不足,因为高PETCO2会增加肺血管阻力,减少肺循环回心血量。但实际上,高碳酸血症会降低脑血管阻力,增加脑血流,上腔静脉回流至肺循环的血量反而会增加。
双向格林手术后的患者采用轻度呼吸性酸中毒(PaCO2 45~55mmHg,pH7.30~7.35)的策略会增加Qp/Qs,提高动脉血的氧合,降低氧耗和乳酸浓度。另外提高吸氧浓度也能够降低肺循环阻力,增加Qp/Qs,应尽量维持SaO2>80%。
若患者术前肺动脉压过高,可持续给予一氧化氮治疗。禁食水和麻醉诱导会导致容量不足,通过监测CVP,维持适当的液体灌注,可增加心输出量,间接增加肺循环血流。实际上,增加Qp/Qs和增加心输出量均可改善SaO2,但Oka等研究表明,在双向格林手术后,提高心输出量比增加Qp/Qs对SaO2带来更强的改善作用。
适当补液维持心脏前负荷对提高SaO2非常重要。SaO2随CVP的升高而升高,当CVP达到16mmHg时SaO2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CVP的升高,SaO2不会再改善。建议在超声引导下经颈内静脉放置中心静脉导管,尽管中心静脉导管的放置可能会损伤上腔静脉或导致血栓形成,但上腔静脉CVP对于该类患者术中的监测非常重要。
当患者出现心跳骤停需要CPR,但标准CPR可能对双向格林手术后的患者作用有限。标准CPR最多只能提供正常血流量的30%~40%,并且有多种因素限制了它对双向格林手术后循环生理机能衰竭患者的有效性。由于本身解剖特点,CPR时该类患者的每搏量降低、肺循环血流量降低、脑灌注降低,因此,患者一旦发生心跳骤停,依靠CPR复苏的机率不高,需要迅速建立体外膜肺进行生命支持。
Ⅲ期手术后行非心脏手术:Ⅲ期手术后的循环系统也称为Fontan循环。Fontan循环患者的评估要包括全面的病史和检查。关注患者的运动耐量、当前药物、手术史、心脏超声或心脏磁共振成像、血氧饱和度和实验室检查。
功能良好的Fontan患者外周灌注良好、温暖,可触及外周动脉搏动,心前听诊应无杂音,SaO2通常在90%~95%(轻微降低的SaO2与冠状窦血液回流到共同心房、通气/灌注失衡或动静脉分流有关)。心脏增大和/或胸腔积液可能预示着Fontan循环的衰竭。
Fontan循环功能差的表现还包括疲劳、运动能力下降、体重增加、心悸、晕厥、SaO2<90%和呼吸困难。这类患者的择期手术应推迟,术前优化措施包括:抗心律失常治疗、正性肌力药物或肺血管扩张剂。Fontan循环的患者体循环和肺循环完全分离,体循环氧合得到改善,同时单心室的容量负荷降低。
Fontan循环围术期管理原则与双向格林手术后相似,包括尽量维持肺循环阻力在较低水平或可能的情况下,维持自主呼吸、维持窦性心律、维持心肌正常的收缩和舒张功能、维持足够的前负荷。与双向格林手术后的循环不同,Fontan循环的体循环静脉系统失去了右心的“回吸”作用,造成体循环静脉压力升高。
体循环压力升高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患者的容量调节能力下降,这是因为脾脏和静脉系统储存人体2/3的血容量,静脉压力的变化对调节循环血量有重要的作用,影响静脉张力的药物、失血、脱水、麻醉诱导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低血压。
由于Fontan循环依赖于前负荷且容量调节能力下降,因此术前禁食水时间要尽量缩短,减少脱水的风险。患者术中尽量维持在Hb浓度>100g/L。出现低血压时可给予血管收缩剂,血管加压素既能够增加外周血管张力,同时也产生肺血管舒张作用,因此将其作为一线药物;去甲肾上腺素常作为二线药物;肾上腺素和米力农可用于治疗心室功能障碍。
另一方面,长期体循环静脉压力升高还会导致肝脏和肾脏功能的异常,术前应仔细评估肝肾功能。肝硬化患者在围术期应考虑麻醉药物药代动力学改变和发生暴发性肝衰竭的可能性。50%成年Fontan循环患者合并肾功能异常,15%合并严重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
非搏动的血流也会导致肺循环肺部末梢血管减少,肺血管床面积降低,血管内皮一氧化氮产生减少,导致肺循环阻力进一步升高,因此应该避免引起肺动脉压升高的因素。降低肺动脉压的措施包括谨慎的使用PEEP、给予较高的吸入氧浓度(FiO2=1.0)、维持较低的PETCO2(这与双向格林手术后的策略不同,双向格林手术后由于肺循环的血流量依赖上腔系统,为使脑血管舒张增加上腔静脉系统回流,常维持相对较高PETCO2;Fontan循环的肺循环血流量不再单纯依赖于上腔系统,通过维持较低的PETCO2,如PETCO2=30mmHg或pH=7.45,可降低肺循环阻力来增加血液回流)。
右心房在长期较高的静脉压负荷下逐渐扩张,最终丧失收缩能力,扩张的心房易发生房性心律失常并成为血栓形成的场所。对于血栓事件高危人群(心房扩张、有血栓病史或房性心律失常的患者),应进行预防性抗凝。术前使用阿司匹林或低分子肝素的患者,建议围术期继续使用。对于术前服用华法林的患者,建议使用低分子肝素桥接。如果必须停止抗凝药,建议尽快恢复。推荐使用下肢循环驱动预防深静脉血栓,特别是对于活动受限的患者。
60%成年Fontan循环患者合并房性心动过速,有术中心律失常史的患者应提前准备除颤电极。很多患者术前携带起搏器,应在术前对起搏器进行程控,并设定一个稍快的心率,这是因为对于有多种其他机制可能降低心输出量和没有内在能力加快心率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设定稍快的心率往往是维持心输出量的方法。
3.小结
单心室患者在不同阶段的心脏手术后都有其独特的循环系统。功能性单心室患者行非心脏手术时,需要熟悉患者的心脏分期手术的方式、术后循环系统的解剖和生理状态,个体化的评估每个患者的心功能和循环状态,才能采取科学有效的麻醉管理措施使患者安全度过围术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单心室不同循环系统模型的研究,探究在不同解剖、通气模式和循环阻力下的最优循环管理模式。在临床上,进行随机对照研究难度很大,队列研究和病例报告分析或许能够给临床医师带来更多的围术期管理证据。
来源:孔昊,马丹丹,张思宇,李雪.功能性单心室患者行非心脏手术的麻醉管理进展[J].临床麻醉学杂志,2022,38(02):207-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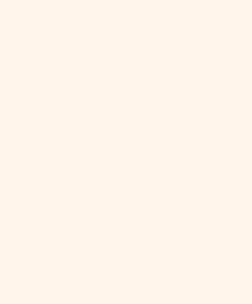
 微信订阅号
微信订阅号
 微信服务号
微信服务号